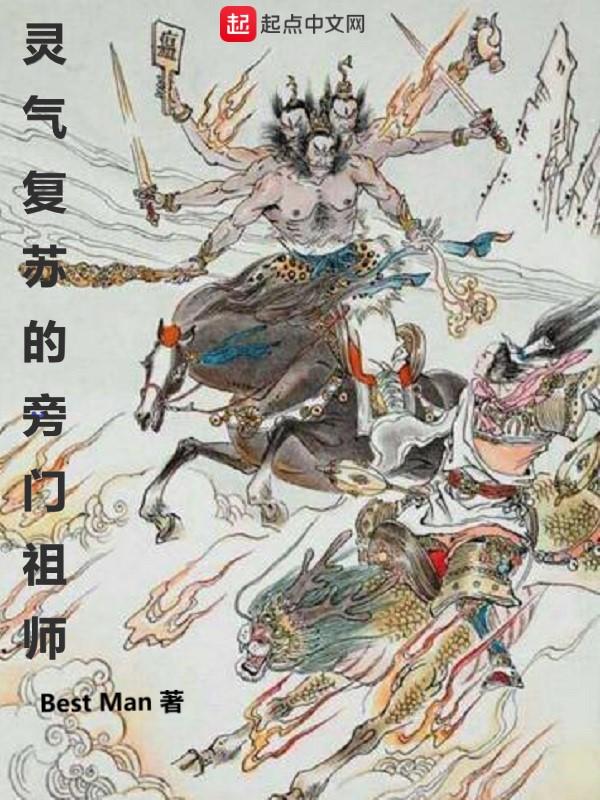《胭脂盆地》停泊在不知名的国度
终年覆盖白雪的Kilimanjaro是非洲最高山,西面峰顶被称为上帝之屋,有一头豹尸僵成一片薄翼,安静地躺卧雪泊。没有人能解释,这头豹跑到这么高的峰顶为了追寻什么。 当飞机抵达戴高乐机场,寒冷的气流如千万支银针刺遍全身,我恐惧冷,因为这种莫名的畏惧而心绪翻腾。那头雪豹蓦然涌现,从海明威的小说里单独逸出,进驻我的胸膛;遂开始在时空坐标中迷航,曾经熟稔的亚热带产雨岛国,肃杀的北地边塞及落英似泣的深山寺院……宛如拍浪袭击,不知此身搁浅何处。在错乱且**的记忆片段中沉浮,那只冰豹像唯一的实体引我靠岸,因感同身受那股无从抵抗的冷而渗出微热。虽然,我仍然不理解它为何攀越雪崖,赴一趟致命追寻。 清晨的巴黎街头宛如被雾封锁的墓场,除了几辆梦游昆虫似的街车,隆冬的冷血...
《胭脂盆地》章节列表
- 人生路口的捕梦人
- 残脂与馊墨
- 第一辑 赖活宣言
- 赖活宣言
- 他们俩
- 大忧大虑
- 给孔子的一封信
- 瓜田启示录
- 老神在在
- 天堂旅客
- 三只蚂蚁吊死一个人
- 第二辑 畸零生活索隐
- 请沿虚线剪下
- 销魂
- 意念传输器
- 黑色忍者
- 幻想专家
- 艺术店员
- 肉欲厨房
- 啊
- 记诵旧景
- 流金草丛
- 第三辑 银发档案
- 老歌
- 春日偶发事件
- 转口
- 子夜铃
- 迟来的名字
- 第四辑 大踏步的流浪汉
- 串音电话
- 黄金葛牵狗
- 面纸
- 当月光在屋顶上飘雪
- 阿美跟她的牙刷
- 密音
- 铁筛
- 终结者
- 临时决定
- 人境
- 果冻诺言
- 胎记
- 不公开的投影
- 计程车包厢
- 古意
- 麦芽糖记录
- 废园纪事
- 暗道之歌
- 大踏步的流浪汉
- 第五辑 停泊在不知名的国度
- 阳光照亮琉璃砂
- 停泊在不知名的国度
热门小说标签
纲吉打排球也是第一最新章节更新内逆旅指什么动物生查子读音是什么青云仕途第一部清宫小仙童 作者上如在线阅读清宫小仙童胤宸txt全本免费最新新婚立规矩?砸婚房改嫁年代大佬免费电影世界大逃亡魔尊为何冒充我未婚夫TXT枯萎的碎冰蓝梗概恶毒女配也会被强制爱吗(末世)by酢浆草全文阅读忆峥嵘岁月谱青春华章手抄报渣男好渣男妙难抵皇妹多娇免费阅读全文正版生查子的查念什么新婚立规矩?砸婚房改嫁年代大佬 在线阅读渣男走了混小子升仙记第一版主青云仕途快穿我靠发疯文学攻略病娇大佬 TXT快穿那个炮灰我穿过偶葱 / 著世界名著大师课免费我看你是长得丑想得美灵媒阴阳簿胡肆临头婚眼花打一最佳生肖生查子·旅思推荐o被a强行标记的纲吉打排球也是第一158逆旅代表什么动物渣男优秀网站tag地图网站地图开局揭皇榜,皇后竟是我亲娘官途,搭上女领导之后!千里宦途升迁之路官道征途:从跟老婆离婚开始权力巅峰:从城建办主任开始官梯险情相亲认错人,闪婚千亿女总裁二嫁好孕,残疾世子宠疯了不乖官路女人香学姐蓄意勾引通房撩人,她掏空世子金库要跑路深入浅出仙帝重生,我有一个紫云葫芦财阀小甜妻:老公,乖乖宠我落伍文学空白在综艺直播里高潮不断官运,挖笋挖出个青云之路!大秦第一熊孩子我靠读书成圣人薄太太今天又被扒马甲了重回2009,从不当舔狗开始万人迷她千娇百媚[穿书]大明:我只想做一个小县令啊官场:从读心术开始崛起逆袭人生,从绝境走向权力巅峰清穿后被康熙巧取豪夺了装疯卖傻三年,从边疆开始崛起官阶,从亲子鉴定平步青云!逆袭人生,从绝境走向权力巅峰小药店通古今,我暴富不难吧?前门村的留守妇女秘书太厉害,倾城女领导直呼受不了一问小说网驾崩百年,朕成了暴君的白月光我和我妈的那些事儿(无绿修改)合欢御女录荒岛狂龙透骨欢爱欲之潮NP直上青云深度补习>上流社会共享女友镇龙棺,阎王命上瘾禁忌爱欲之潮假千金身世曝光,玄学大佬杀疯了臣服议事桌上的官途:权力巅峰开局手搓歼10,被女儿开去航展曝光了!关于我哥和我男朋友互换身体这件事村野流香闪婚夜,残疾老公站起来了师娘,你真美迟音官妻太荒吞天诀乡村绝色村姑九天剑主春漾穿成虐文主角后我和霸总he了日复一日真千金霸气归来,五个哥哥磕头认错机娘世界,校花老师要上天了农门医女:我带着全家致富了大明:诏狱讲课,老朱偷听人麻了四合院:带着娄晓娥提前躺平蛟龙出渊,十个师姐又美又飒!被骂赔钱货,看我种田跑商成富婆悟性逆天:模型机悟出龙警3000!脱下她的情趣内衣山雨欲来离婚后,渣爹做梦都在偷妈咪小夫人奶又甜,大叔彻底失了控我委身病娇反派后,男主黑化了图谋不轨七零甜蜜蜜,糙汉宠翻小辣媳末世:开局疯狂囤物资,美女急哭了千亿总裁宠妻成狂病弱太子妃超凶的医妃她日日想休夫放开她,让我来财阀小娇妻:叔,你要宠坏我了!万人嫌的大师兄重生后,天道跪舔神医毒妃腹黑宝宝镇南王女总裁的贴身高手重返1987携空间嫁山野糙汉,暴富荒年官运,挖笋挖出个青云之路!修仙暴徒九龙乾坤诀官道雄途镇国狂龙盖世狂龙天剑神帝婚后热恋宦海官途:从撞破上司好事开始苟着苟着我成了反派真爱狂医下山,都市我为王官道升天官道之破局闪婚女领导后,我一路青云直上快穿之我在年代文里抱大腿帝剑天玄诀胭脂盆地全文免费阅读最新章节更新 胭脂盆地经典语录 胭脂盆地讲的是什么 胭脂盆地简介 胭脂盆地免费阅读 胭脂盆地你的眼睛 胭脂盆地摘抄好词好句 胭脂盆地txt 胭脂盆地作者 胭脂盆地有吗 胭脂盆地解说 胭脂盆地收录在哪本书 陷入绝境的女退魔师们 沉睡亿万年,苏醒即无敌 黄毛在哪里 阿米娅究竟是什么时候变成了病娇重女呢? 曹贼 最后一战(彩插双语版) 万艳护道录 无限扭蛋机 女儿红 狮子、女巫和魔衣橱(彩插双语版) 偶然碰见欲求不满的阿尔忒弥斯团长在自慰?那就将她调教成自己的专属母狗吧~ 黎明踏浪号(彩插双语版) 青梅嫁给表哥 红楼探玉 争夺(H) 我有一剑 数理化通俗演义(插图版·全5册) 凯斯宾王子(彩插双语版) 能言马与男孩(彩插双语版) 银椅(彩插双语版)
本月排行榜
- 娱乐圈之风流帝王北斗星司
- 美母的诱惑大唐妖僧
- 美母如烟,全球首富佚名
- 韵母攻略流浪老师
- 智娶美母纯绿不两立
- 后宫催眠日记十六夜天
- 熟女记卡牌
- 原来,她们才是主角(加料版)CCC
- 妈妈的欲臀(重生之我的美艳教师妈妈)佚名
- 催眠系统让我把高冷老师变成性奴肉便器佚名
- 娱乐圈的曹贼大龙很帅
- 重生之娱乐圈大导演开飞机抓仙女
- 红颜政道饿狼咆哮
- 继女调教手册(H)奶油味香蕉
- 四方极爱Howlsairy
本周收藏榜
- 重生之娱乐圈大导演开飞机抓仙女
- 父债子偿拉大车的小马
- 妈妈陪读又陪睡佚名
- 豪乳老师刘艳tttjjj_200
- 妈妈又生气了白奉羽
- 四合院之啪啪成首富雨是苍天在哭泣
- 我的道家仙子美母月在荒
- 带着美艳医母闯末世画纯爱的JIN
- 美母的信念大太零
- 美母如烟,全球首富佚名
- 原来,她们才是主角(加料版)CCC
- 无限之邪恶系统永恒的恒星
- 我的人渣指导系统(加料版)薛定谔的猫耳
- 我的教授母亲(高冷女教授)大包子
- 无限之生化崛起三年又三年
最新更新
- 逃荒就逃荒,最后逃成了皇帝?是李
- 劣质依赖松针牡丹水
- 穿越后,系统:宿主,你不是路过吗?楠忘今萧
- 玉阶囚潮从
- [崩铁]开局成为卡厄斯兰那的弟弟原初观星者
- 困兽(bg+bl)观山客
- 姜家全职女儿日记得无
- 秽土重生芬陀利华
- 琴缘俱乐部江城子和溪村客
- 我死遁归来,好兄弟他不装了水耳
- 躺平修仙:道侣修炼我变强张知守
- [综英美]你家攻略任务是这样的?璃九笙
- [剑三]带着甜甜温泉山庄称霸异世界山中梦客
- 七五吃瓜手札: 我在年代文里卷成亿万富翁载酒晚辞
- 游戏降临:我靠捡垃圾路路通可爻
新书入库
- 绝望的直女高山风雪
- 伪神也要救世吗?[万人迷]魂安
- 消失的画中人林暮烟
- 末日捡了个Omega木槿要吃班戟
- 女装混入魔法学院后[西幻]陈二掌柜
- 她不爱太子了云川雪青
- 修仙:从种田收获奖励开始长生吾旗
- 顶A上校,您的Beta甜心跑了!橘甜水泥猫
- 如何养歪一只剑灵甜饼样本
- 没用的omega[GB]青云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