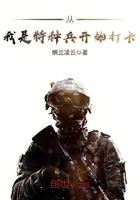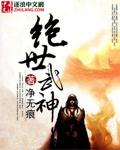手机浏览器扫描二维码访问
赠蒋秉南序(第1页)
赠蒋秉南序
banner"
>
清光绪之季年,寅恪家居白下,一日偶检架上旧书,见有易堂九子集,取而读之,不甚喜其文,唯深羡其事。
以为魏丘诸子值明清嬗蜕之际,犹能兄弟戚友保聚一地,相与从容讲文论学于干撼坤岌之际,不谓为天下之至乐大幸,不可也。
当读是集时,朝野尚称苟安,寅恪独怀辛有索靖之忧,果未及十稔,神州沸腾,寰宇纷扰。
寅恪亦以求学之故,奔走东西洋数万里,终无所成。
凡历数十年,遭逢世界大战者二,内战更不胜计。
其后失明膑足,栖身岭表,已奄奄垂死,将就木矣。
默念平生固未尝侮食自矜,曲学阿世,似可告慰友朋。
至若追踪昔贤,幽居疏属之南,汾水之曲,守先哲之遗范,托末契于后生者,则有如方丈蓬莱,渺不可即,徒寄之梦寐,存乎遐想而已。
呜呼!
此岂寅恪少时所自待及异日他人所望于寅恪者哉?虽然,欧阳永叔少学韩昌黎之文,晚撰五代史记,作义儿冯道诸传,贬斥势利,尊崇气节,遂一匡五代之浇漓,返之淳正。
故天水一朝之文化,竟为我民族遗留之瓌宝。
孰谓空文于治道学术无裨益耶?蒋子秉南远来问疾,聊师古人朋友赠言之意,草此奉贻,庶可共相策勉云尔。
甲辰夏五七十五叟陈寅恪书于广州金明馆。
请关闭浏览器阅读模式后查看本章节,否则将出现无法翻页或章节内容丢失等现象。
- 不良娇妻:老师,晚上好简小沫
- 斗罗大陆之极限后宫(无绿改)3250027607
- 端庄美艳教师妈妈的沉沦无绿修改版佚名
- 女配她只想上床(快穿)黄心火龙果
- 马屌高中生穿越到性观念开放的世界热爱生活的小东
- 吾母美如画曹主任
- 四合院之啪啪成首富雨是苍天在哭泣
- 美母的诱惑大唐妖僧
- 红颜政道饿狼咆哮
- 亮剑:开局拿下鬼子据点我在赚钱
- 黄心火龙果小说笔趣阁黄心火龙果
- 熟女记卡牌
- 房客(糙汉H)无罪国度
- 配种(1V1,SC)豌豆荚
- 穿越影视万界之征服壹樂
- 一屋暗灯麦香鸡呢
- 可以帮我补习吗卷心菜
- 被健身房教练秘密调教后百无禁忌
- 众香国,家族后宫瘦不了
- 后宫催眠日记十六夜天
- 人生如局笔龙胆
- 悖论流苏
- 斗罗大陆之催眠武魂玖粮
- 神豪的后宫日常大香蕉
- 斗罗大陆修炼纯肉神梦斗灵
- 我丰乳肥臀的瑜伽教练母亲和保守的翘臀长腿女友被得到催眠APP的猥琐大叔调教成了专属肉便器世界在跃动
- 妈妈又生气了白奉羽
- 斗罗大陆2蚕淫小六六
- 娱乐圈的不正常系统(修正版)霸王色
- 美母如烟,全球首富佚名
- 四合院之啪啪成首富雨是苍天在哭泣
- 原来,她们才是主角(加料版)CCC
- 无限之邪恶系统永恒的恒星
- 常识修改:拥有催眠能力的我,将整个学园都进行常识置换你的性癖手册
- 仙子的修行karma085
- 租赁系统:我被女神们哄抢!OVA
- 我的道家仙子美母月在荒
- 重生之娱乐圈大导演开飞机抓仙女
- 冷艳美母是我的丝袜性奴佚名
- 蛊真人之邪淫魔尊千面兰
- 我的冷傲岳母和知性美母因为我的一泡精液成为了熟女便器 (无绿版)hanshengjiang
- 我在魔兽世界当禽兽晨世美
- 邪恶小正太的熟女征服之旅疯狂的笨笨
- 人妻调教系统淫妇章鉴
- 我在三国当混蛋三年又三年
- 肥宅肏穿斗罗大陆清酒
- 穿越影视万界之征服壹樂
- 影综:人生重开模拟器娱乐圈老司机
- 叶辰风流(幻辰风流)瘦不了
- 乱伦豪门杨家假面阿飞
- 为初恋他爹守寡后兰山姑娘
- 她在江湖钓了个剑客与千春
- 我带萨摩耶杀穿末世晚熟稻
- 七砚墨芝木桃
- 非典型忠犬请怜爱秋鹤知
- 万古第一至尊天机红辰
- 校花表白后,青梅后悔哭了原始罪孽
- 别惹胆小鬼崔又生
- 你想当皇后吗妙龄鲨鱼
- 进阶大帝,退婚师妹悔哭了我特别白
- 你攻略的那个,是反贼!允青
- 戏精穿越成古代万人嫌兰烟寻
- 你再跑我要ptsd了叔戊
- 暮昌之美人灯小米辣爆炒朝天椒
- 门第连谏
- 七个师姐皆大佬,我出世即无敌当空皓月
- 被京圈太子猛追后,前任红眼喊大嫂江有鱼
- 皎皎月光夏小檀
- 忍婚连谏
- 让你去养老,怎么救世了?不予尘
- 重回九六之小城日常一枝甘露
- 末世大佬靠吃播爆红现代星空作毯
- 穿书后她沉迷养雪豹[女强]白心石榴
- 都市之我有无敌修改器大扑街
- 家有遗产连谏
- 时空订制全球华语科幻星云奖组委会
- 洛克菲勒自传约翰·D·洛克菲勒
- 祝酒辞大全吕双波
- 你是自己的全世界乔子青
- 场景致辞与即兴发言卢敬天
- 沟通的艺术高文斐
- 霍格沃茨:不捲你学什么魔法佚名
- 海伦·凯勒自传海伦·凯勒
- 林肯传戴尔·卡耐基
- 水浒可好玩了(全2册)小葛兮兮
- 少年读诗经:足本风雅颂(三卷套装)白羽
- 高情商语言训练课夏季
- 你的任性必须配得上你的本事米苏
- 给你一个团队,你能怎么管赵伟
- 婚姻心理学:你要的是幸福还是对错于思成